那是一個彷彿置身於地球之外的小行星,從市區騎車到這裡需要整整一個多小時的路程。
大片的綠蔭、寧靜的街道,以及三三兩兩坐在門口聊天乘涼的阿公阿嬤們,構成了這個村落隨處可見的景象。
傍晚,橘紅色的晚霞映在這個只剩下寂靜的小地方,太陽才下山,村子裡的店家就陸陸續續拉下鐵門。才不過晚上八點,整個村子就像進入了深度的睡眠,只剩下零落的狗叫聲和兀自閃爍的紅綠燈,像是在向經過的路人提醒這個村子還有呼吸。
他在國小的時候隨著改嫁的母親,一起來到這個地方重新開始生活。
他不愛念書、不準時上課,有時與同學打架,有時也會偷班上同學的東西,而且幾乎每一天都是到了中餐時間才會出現在教室。
母親與繼父每天都會到外地工作,直到深夜才回家,放學後他就握著母親給他的生活費自己到村子裡唯一的麵攤或自助餐店吃飯。
繼父厭倦了經常被老師傳喚到學校細數孩子在學校的種種行為,有一次索性在電話這頭將揍他的聲音完完整整的傳遞給老師,嚇得導師從此不敢再打電話到他們家討論他的狀況。
我問他為什麼上學經常遲到?
他說,因為晚上睡不著,為了避免被家人發現,所以他就從房間的窗戶跳出去閒晃,直到天空快要翻出魚肚白才又悄悄回到房間睡覺。
有時候他自己一個人在空盪盪的大街上漫無目的地走著,有時候則是坐在村子裡唯一的便利商店前,用省下來的晚餐錢買一顆熱騰騰的肉包子,撕成小塊餵給和他一樣還醒著的流浪狗,順便也和牠說幾句話。
我說,那好像是一種叫做「寂寞」的感覺。他點點頭。
很寂寞,但好像也已經習慣了一個人的生活。那些所謂的信任與關愛,在一個人的世界裡全都是遙不可及的奢求。
黑夜裡,少了謾罵與責備的聲音,這世界安靜得像是只剩下自己。
「做人不必太認真啦⋯⋯」他罕見地收起一貫的調皮,有些認真地說:「反正也沒有人會了解。」
對於這種青春期憂鬱的感慨,有時候我會選擇輕鬆以對。
「少年不識愁滋味,為了耍帥強說愁。」
為了凸顯自己的特別、為了宣示自己已經長大,所以在青少年的書包或筆記本經常會看見用原子筆精心描繪的「愛錯」、「悔恨」、「惜緣」等充滿情緒性的字詞。
但是,此刻我卻只是靜靜地聽著。因為我知道,這很可能是他在諮商室裡最難啟齒的一句話,也是讓他最難接受的現實。
在這個家,他的聲音沒有容身之處。
他曾經使用各種方法表達他的想法與情緒,但忙碌的大人根本沒時間聽他說話,也沒空坐下來好好理解他。他經常會用一雙靈巧的雙手和不受拘束的創意,將許多壞掉的玩具回復原貌,將許多平凡無奇的東西變化出不同的玩法。幸好擁有這個專長,他常常能夠探索出許多好玩的事情來陪伴自己的寂寞。
但是不知道是不是依舊難抵寂寞的侵蝕,他說他開始覺得玩什麼都無聊,做什麼都覺得沒有意義,所以開始去破壞東西、偷東西。然後他頻繁地進出警局,直到最後被法院判了保護管束。
「我可以怎麼稱呼你?」我問。
「隨便啊,叫我咖哩好了,我籃球超強的。」他露出不可一世的笑容。
「那你的導師或同學都怎麼稱呼你?」
「他們跟我不熟。」他聳聳肩。
「那你媽媽或繼父怎麼稱呼你?」
「×咧,他們差不多快忘記我了吧?」
說實話,我很難想像一個孩子到底過著什麼樣的生活、經歷過哪些事情,為什麼會感受到自己居然被最親近的爸媽給遺忘了?
***
深夜,我在鍵盤上仔細敲下和他談話的諮商紀錄,音響裡傳來萬芳的〈夜照亮了夜〉,悠然沉靜的旋律與歌聲帶我回到那一段有些慘澹的童年回憶:
夜是那麼黑,看不見悲喜界限
任誰都好累,青春只剩一點眼淚
我變成了誰,不自由為愛放逐靈魂
心死就不傷悲,明知愛很珍貴⋯⋯◇
{心理諮商小教室}
關於諮商紀錄的撰寫,為求保密,諮商師通常會在機構內就寫完當次的紀錄。有些機構甚至會設置寫紀錄專用的電腦,並且禁止上網的功能以確保紀錄不會外流。但我天天騎車穿梭在不同的學校之間,如果不把握時間記下來,等我回到辦公室早已忘了幾天前的談話內容。為了避免忘記諮商的重要片段,在接案的途中,我會在便利商店找個隱密的角落或者晚上回到自己的房間盡快完成紀錄,並且謹慎保存。
——摘編自《遇見,生命最真實的力量:一個諮商心理師的修練筆記》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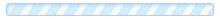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