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他躺在冰櫃裡已經十年了,死的時候是四十二歲。2008年2月6日,他因「奧運安保」被抓進看守所,八天後死亡。他年邁的老母親至今都以為他還活著。
他是一個樂手,畢業於北京大學。
在公開場合,他的名字不再被他的樂隊提及,換了樂手的樂隊,目前仍活躍在中國大陸樂壇。他的很多朋友、同學不能公開紀念他,對他的死諱莫如深。
他的名字被中國官方網站屏蔽,他叫于宙。
2
1966年5月20日,于宙出生在中國東北松源的紅旗農場五隊,也叫七家子,位於前郭爾羅斯蒙古自治縣,隸屬於吉林省。
小時候于宙就比一般孩子傻,于宙的姐姐于群介紹,「他個子比同齡孩子高,但有孩子打他,他也不會還手。我替他報仇,找機會把那孩子給揍了,他還不領情,說你打他幹嘛呀?稍大一點的時候,村裡有人家宰牛,他還會為牛哭起來,我們那時都笑話他。他還木呆呆的,吃的啊、玩的啊,什麼事都不往前搶,也不爭,那時候東西少……」
十一歲時,于宙全家搬到了長春農安縣。1985年,他考上北京大學西語系法國文學專業,他是當地的文科狀元。
當于宙帶著少年的文學夢想來到北京時,北大作為精神意義的象徵,已經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1950年代,北大的院系調整及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文革時期的大字報、打老師,及後期「梁效」(即「北大、清華大批判組」的化名。──註)的「批林批孔」,使北大學人的尊嚴早已喪失殆盡。1986年開始肅清「資產階級自由化」,那之後北大的自由,就更多體現在男女交往的隨意,及西方現代文藝思潮的自由湧進了。
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離經叛道讓學生們興奮不已,追求個性解放的文學藝術當時成為主流,先鋒的、實驗的文藝演講在北大到處都是。于宙從不激烈地反對什麼,他的口頭禪是「我是農村人,不太懂」。當時也在北京上學的于群說,「他不願故作高雅,所以才強調自己是農村人。其實我父母都不是農民,我父親農大畢業,我母親是小學老師,我家有非常多的外國文學書,也是因為他看了很多書,才想到北大學法國文學的。」
當大家想著將來幹什麼、怎麼發展時,于宙吊兒郎當,找女孩談談戀愛,或者彈彈吉他。一些在別人看來很不現實的東西那時就開始困擾他了,他當年的一段詩留下來:
走啊走
走到一個大門口
推開了門
往裡面看
裡面什麼都沒有
「一點詩意沒有」,多年後他妻子許那回憶,「但嚇了我一跳,修煉後我才能理解它。」
3
1989年,北大學生的政治熱情開始高漲,他們希望中共能夠在內部改進,能夠更加民主、自由。臨近畢業的于宙,和大多數學生一樣,該去的地方他都去,三角地看小字報,遊行,天安門廣場也去了,「總是要去支持的」。但他對國家大事沒有熱情,也不喜歡政治,6月4日之前他就趁亂到農村玩去了。
畢業時國家安全部曾去他們系挑人、政治審查,于宙不想去:「祖宗八代都查,那不就是當特務嘛。」最後他選擇到北京外文局當翻譯。
外文局是中共對外宣傳的喉舌,他所在的《北京週報》法文部就是周恩來親自命名的。于宙喜歡奧林匹亞打字機的聲音,「像音樂一樣悅耳」,但翻譯中共領導人的講話讓他厭煩。當時如果想掙外快,還可以加班翻譯《鄧小平文選》。
工作之餘,剛剛畢業的大學生經常搓麻將玩撲克牌,那是六四以後嚴酷的政治氣氛中,最為放鬆的流行娛樂了。于宙不會搓麻將,大多時間就是撥拉一把吉他,有時和朋友褚福軍等聊聊文學。(褚福軍,又名戈麥,北大中文系畢業的詩人,當時在外文局工作。──註)
1991年,褚福軍負石塊自沉萬泉河,這讓于宙很有感慨。他後來說,如果沒有真正的信仰依託,沉浸在純藝術裡的人生其實也是沒有出路的。
在北京城的于宙,執著地想念著他出生的地方,他經常閃著單眼皮的小眼睛,孤獨地吟唱:
總是在夢裡,
又回到老地方……
他出生的地方只有幾十戶人家,家家都敞著門過日子,不太擔心丟東西,東西被偷也知道是誰幹的。
他說起村裡的蘆葦塘,裡面有大天鵝,叫「長脖子老等」,「沒啥稀罕的,北京也會有」。有一次,在北京一條發臭的護城河邊,他堅持說不遠處的石頭上,站了一隻「長脖子老等」。朋友和他打賭,走過去一看,果然不是,一個灰色塑膠袋纏在了水泥澆灌的石頭上。
多年後他回老家找,也沒看到一隻「長脖子老等」,他喜歡的東西都消失了。
不能適應機關生活的于宙總被領導「談話」,最嚴重的違紀是:沒有經過申請,他就和外國專家私自接觸。領導也沒把他咋樣,他倒是決心自動離職了,那時候,和他一起進外文局的同事,靠翻譯《鄧小平文選》,農村老家都快蓋上房子了。
4
1991年,于宙從外文局離職下海,當時也不是想賺什麽大錢,他只是想換一種生活。
「我們都認為他沒有做生意的頭腦,有時還缺心眼。」一個北大同學回憶,但出乎意料,他賺了大錢,「他是頭一個用手機給我打電話的人,我記得太清楚了,因為那時候大家也只有個數字呼機(俗稱BB.Call)。我能在電話裡聽到呼呼的風聲,他在街上給我打電話!那年代,不可想像啊!」
拿著磚頭一樣的「大哥大」,叼著雪茄,于宙成了一個「倒爺兒」,前呼後擁,每天都是飯局,然後帶客戶到酒吧唱卡拉OK。他經常唱《凡人歌》:「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間,終日奔波苦,一刻不得閒。既然不是仙,難免有雜念,道義放兩旁,利字擺中間。」
開始還牛哄哄的他很快就感到痛苦了,那段日子後來被他唱成了搖滾:
錢是好東西
名是好東西
可是除了名和利
在人群之中又能得到什麼東西!
為何不逃離
能不能不去……
他對許那說,不想做生意了,「我想幹自己喜歡的事情」。
常去的酒吧裡,一對駐唱的北漂歌手吸引了他,他羨慕不已:像他們那樣生活多好,不用花錢唱歌,還能賺錢!幾年後,他與這對北漂的小娟和黎強夫婦組建了民謠樂隊。
5
他要搞音樂,1994年從北京飯店撤了出來。他的同學再次吃驚:「居然又玩上搖滾了,于宙連譜都不識!」不識譜的他靠錄音機寫歌,腦袋裡一有了旋律,馬上就打開錄下,找樂手排練、演唱。他參加各種聚會,與各種人接觸,每天都好像要出去找什麼,然後是每天都找不到。他寫的歌也沒人能理解:
當我發現自己的時候,
正在跟著人群往前走
……
再回頭看看我的所有
面對死亡就是一堆垃圾
可我還沒有找到什麼東西
能讓我投入心甘樂意
他總是不合時宜,他的同學說,我們不懂他。他不愛說話,心裡有主意,不太和人說心裡的想法。
折騰了兩年,于宙最後否定了他所有的搖滾作品,他認為音樂「不應該是宣洩」,而且,搖滾圈裡一些奇奇怪怪的事兒也讓他越來越疏離,他說,「我心中是有淨土的」。
6
1997年于宙接觸了法輪功,剛開始就發生了奇蹟。當時他椎間盤突出,連幾斤重的米都抬不了,看《轉法輪》不到一個月,他就能背一個人上六樓了。但這還不是他要修煉的根本原因。
他興奮地告訴朋友:「我有師父了!我知道生命的意義了……」
不是所有人都關心這個。他笨嘴拙舌,說話又慢,被搶白一通後,也就默默地給侃侃而談的朋友們端茶倒水了。他不氣惱,也不辯解。他的真誠和孩子氣,讓習慣了插科打諢的朋友們也不忍心嘲笑他。
在一個小本子上,他工工整整寫了這句話:你是否正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對人好。
還有一句歌詞後來被發現:
當我發現自己不屬於這個世界
我決定與它和平共處
他寫字一筆一畫的,他學不會連筆字,瀟灑不起來,以至後來在CD上給粉絲簽名,也笨拙得很。
7
「師父把我從地獄裡撈出來,洗乾淨。」有一天夜裡打坐後,于宙說:「真正的覺者,是能為真理而赴湯蹈火的。」那是1999年初,許那回憶,當時他表情肅然,像小學生一樣,手放在自己的心口。
1999年7月20日,法輪功被中共定為「×教」後,全國各地有大量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上訪。很多外地學員在于宙家有過短暫的停留。于宙帶回了學電腦的黃雄來家裡交流,吉林大學數學系教師沈建利和她兩歲的女兒格格、工程師雲慶彬夫婦和他們的小兒子、大連輕工學院的陳家福等等,都在他家住過。武漢的彭敏那時也偶爾到他家洗個澡,晚上彭敏在菜市場的攤位上睡覺。
于宙有時開車把學員送到天安門,然後到樂隊排練。晚上演出後,有時會往家拉違禁的書和資料。有一次,他拉了一後備箱的《法輪功》,到家後說:「我害怕,總感覺警車在後面嗚嗚跟著。」但下一次讓他去拉書,他還是毫不猶豫。
那時他家最多一次住過五、六十人。警察來了,抄家。人不斷被抓走,被拘留、被判刑、被勞教。于宙也被拘留了兩次。
2001年4月,彭敏死了,二十二天後,彭敏的母親也死在同一家醫院。看到消息後,于宙異常嚴肅,對許那說:「將來我們兩個不管是誰,如果是因為修煉而死,另外一個人一定不要難受。」
8
不久,許那遭判刑五年,罪名是「利用邪教組織迫害法律實施」,那次如果不是于宙出去排練,也會一同被堵在家裡的。
于宙對監獄警察直言自己也修煉,所以就幾乎得不到探視妻子的權利。唯一有一次電話接見,隔著玻璃,他拿著話筒對許那說:「你過得比我更有意義。」那五年,于宙與樂隊一起,繼續排練演出。
一位粉絲朋友後來接受採訪時回憶:「我一直不知道于宙家裡的事。但那天他特別高興,說第二天他妻子就要回家了,說她在監獄已經整整五年了。接著于宙就談了他們的信仰,而且他說了一句話,後來我才反應過來,當時我以為他不過就是說說罷了。他說:『我是能為信仰付出生命的。』」
那時樂隊已經有了名氣,評論說,他們樂隊用音樂搭建了一個世外桃源,閉上眼睛聽他們的音樂,好像就進入了林中山谷,就可以遠離世俗的煩惱。樂隊名字叫「山谷裡的居民」。
9
2007年11月16日,樂隊在中國傳媒大學開始了巡演的第一站。最後的壓軸曲目是于宙唱的。他自己吹口琴伴奏,翻唱了羅大佑的《愛的箴言》:
我將生命付給了你
將孤獨留給我自己
我將春天付給了你
將冬天留給我自己
……
他神情漠然,沒有一絲煽情,也沒有與台下互動。一個在場的學生說,傳媒大學的舞台,一般人鎮不住,最後一曲都會被習慣性惡搞,不管有多大的名氣都會被噓。很奇怪,那天台下的學生居然沒人起哄,也不知于宙怎麼就鎮住了場。
10
兩個多月後的一個晚上,于宙與許那開車回家,路上被警察攔截。他們的身分證號碼被當場聯網查驗,很快證實他倆均修煉法輪功。警察在于宙的吉他袋裡找到了幾張神韻光碟。那一夜,他們作為「同案」被扣在派出所訊問。那是中共「創建平安奧運」的第一天──2008年1月25日。
許那回憶:
「第二天我們被拉到醫院體檢,之後在通州看守所門口再次體檢,體檢合格才可以被拘留。在羈押室門口,走在前面的于宙突然就停住了,轉過身對我說:『這一次,我將以生命為代價。』他表情僵硬,看著我,又說:『你放心,我行。』
「進了羈押室,他什麼都不配合,我聽見他對警察說:『我沒有罪』,警察對他吼起來……那幾天南方爆發了特大雪災,北京也奇冷無比。」
八天後,于宙的在京家屬被通知「于宙病危」,他們趕到北京999急救中心,但不許接近于宙的身體,周圍擠滿了黑衣警察。當晚十點,于宙被宣布死亡,警察稱死於糖尿病。
那是除夕之夜,北京城的鞭炮不停歇地炸響,讓人心慌。于群說:從那以後,我再聽不了鞭炮聲了。後來于宙在她的夢中出現,對她說,「姐,不要難受,死,只不過是在世間脫下了一件衣服。」
隔著看守所的柵欄門,警察對許那宣布了于宙的死訊,她沒有掉一滴眼淚。第一次被判刑時,她的「同案」、法輪功學員李麗死在看守所;這次的「同案」是她丈夫,又死在看守所。她想起了丈夫曾對她說的那句話:將來我們兩個不管是誰,如果是因為修煉而死,另外一個人一定不要難受。
許那就于宙的非正常死亡向通州看守所提出了控告,因其是法輪功修煉者,檢察院「不予受理」。 之後她再次被判刑三年。
于群則要求警方出示當時的監所錄像,警方開始說,「可以給你看一部分」,後來又說,「錄像都刪了」。
「于宙被拉到醫院前,每天我都和他在一起。」一個與于宙同監室的在押人2011年出現了,他聲稱見證了于宙在看守所最後的日子。
「他受的苦不是人受的」,他豎起大拇指,「于宙是一個爺們!沒見過這麼剛兒的爺們!」這個不願公開姓名的人還說,「通州看守所草菅人命,責任警察叫董亞生,會武術。」百度網上查到,董亞生曾被評為全國優秀警察,是警察系統內的武術冠軍。
11
他不想死,但他決絕做出了一個決定:「我將以生命為代價。」
在此之前,他認識的一些修煉者有罹難的,包括沈建利;還有黃雄失蹤十五年都沒有消息;陳家福和彭敏被打死;參與長春插播的雲慶彬被逼瘋,他的妻子也因為不認罪遭受酷刑。他當然非常清楚,他的選擇可能是「要拿命去換的」。
他的北大同學說,于宙生活的每一步都出人意料,但他的死,確實很難接受,因為「他不是叛逆的人,也不偏激,他性格忍隱,甚至很柔弱,不會與任何人為敵」。
他只是堅持:「我沒有罪」,他只不過單純地把自己的思考和生命實踐、融貫在一起,試圖以肉身去承擔這個結果。
當普通人已經無力抵擋國家機器的碾壓,當努力適應環境成為實利教育的目的,當趨利避害地遊刃有餘於現實成為一種智慧,當集體噤聲、選擇性遺忘、顧左右而言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常態,作為北大學子,于宙死的一個意義就突顯出來:一個人僅僅為堅守一個最基本的常識,就可以付出生命的代價,而更多的人,還沒有能力去面對這一最簡單的問題。
于宙死後一直躺在冰櫃裡,他的名字被中國網站屏蔽,所有與他相關的文字、影片幾乎都被刪除。而在一個老式卡帶裡,還能放出他二十多年前的哼唱:
我已經活了一百來年
一個無奈的軀殼
一個混亂的空間
是不是在我離開以後
天與地仍然會不停地轉
……
感謝所有接受採訪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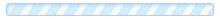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