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讀小學的時候,在進入校門的右側,有一棵張著大傘、枝葉繁茂的大榕樹。初初進入學校,覺得一切都是有點陌生、有點膽怯,不敢冒然接近。只有那棵大榕樹下有個大綠蔭,大人小孩都可以在樹底下,或嬉戲、或聊天、或等人,彼此誰也不會拒絕誰,誰也不會干涉誰。所以那時讓我最放心接近的地方,就是那棵老榕樹。
低年級下課時,第一個瞄準的目標就是那棵大榕樹。我們可以在下面玩跳格子,玩官兵捉強盜,可以無聊地聊天,也可以呆坐著看別人遊戲。等到中高年級後,我還是常把下課的第一個目標,瞄準在那棵大榕樹;和同學們爬到樹上玩「鬼捉人」的遊戲,大家憑著敏捷的身手,冒險的精神,靈活的攀爬和穿梭在樹幹之間,刺激又有趣。
雖然老師們三令五申的禁止我們在樹上活動,但是茂密的枝葉,剛好擋住老師的視線,也擋住炙熱的陽光,更擋住外面的風風雨雨,所以即使有人摔斷手腳,但是那棵大榕樹,還是我們擁有最多歡笑、最常光顧的地方。
離開小學,每每經過一段時間,偶爾總會想回去校園裡走走。當年的老舊教室翻修成巍峨校舍,花園裡百花齊放,操場不再泥濘,走動往來的人們都已是陌生臉孔。記憶裡唸它戀它千百回的,都已是另類風貌,唯獨老榕樹是依然翠綠無比,香菇般的造型依然熟悉顯眼,只是在樹下逗留的人已寥寥可數了。
住家不遠的公園,也有一棵大樟樹,是來自四方的年長者的聚會所。早上有一群人在樹下練功,彼此共存共榮,各取所需;有人輕步挪移,有人虎虎生風;有人閉目養神,有人旁若無人。中午,有三兩長者,在樹下乘涼打盹,或坐或臥,也有竊竊私語者,說個沒完沒了。
約是午後3、4點之間,人們開始逐漸聚集,小販也應運而生。有人賣菜、有人賣膏藥、有人賣衣服、有人賣小吃,老人們聚集圍觀,你挑我選,詢價者多,成交者少,不過彼此倒也談笑風生,自得其樂。
大樟樹的枝葉,擋住陽光,遮住小雨,給了社區附近的長者們一個聚會的天地。老樹經歷歲月,老人嘗過風霜,兩者原本是沒有交集的平行線,但是在對的時光,他們相遇所激起的火花,卻豐富了相互的價值與韻味。大樹高高的撐起它的枝葉,抵擋風雨,守住寂寞,海納四方的長者們,穿梭其間,悠遊其間,迎來送往,不曾懈怠。
從小到現在,在我心底也一直珍藏著一棵大樹,那就是我心中最尊敬的父親——永遠無法忘懷的父親身影。沉默木訥的父親,從小和孩子們的交談不多,童年的印象中,他就是像陀螺般不停工作的化身。
天沒亮就出門,半夜還沒能回家,拚命的先做好自家的農事後,還要搶時間出門去打點零工,貼補家用。食指浩繁的家庭開支,把父親硬是由英挺變成微駝的身影,或也是如此,所以要看到父親開懷大笑的機會,總是遠比愁眉不展的機會少得多。
小學畢業之後,他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只能陪著爺爺耕作向地主承租的田地;為了全家生計,身手矯捷的他,即使聰穎過人,也只能畢生周旋在「看天田」的翻攪中打轉。在那個嚴格淘汰的升學年代,在父親「再怎麼窮,也不能窮孩子」的信念裡,我們兄弟三個傲人的升學成績,更壓得父親連一點喘息的機會都沒有。
印象最深刻的是父親帶著我們插秧、除草、割稻時,額頭上的汗水可以越過三道深烙的皺紋,沿著他面頰而汗如雨下;帶著我們歷經溽暑酷寒、歉收貧困、賒借讀書的十餘年歲月裡,沒有任何憤怒怨懟,只有沉默地堅忍咬牙應對。
讀書不多的他,卻是祖父的好幫手和家庭的大支柱,更是鄰里親人間,爭執與糾紛的仲裁者,而兩任的鄉民代表,也使得他扎實的為地方盡了一些力量。
在那個貧窮的世代,在偏鄉的地方,他能教養出幾個大學畢業的出色孩子,在鄰里中,本應可以昂首抬頭地面對那些一向不看好他的親友們,但他總是低調謙虛地面對大聲嘲笑過他的街坊鄰里,還聲聲交待我們要學會敦厚謙卑地服務他人,做個有風骨、有情有義的漢子。
成長後接受社會歷練的我,每每面臨考驗與挫折時,首先閃過腦際的就是父親的身影、言行和聲聲叮嚀。父親沒有顯赫的家世,對我們沒有嚴厲的訓斥,也沒有瑰麗的讚美,只有那終年的赤腳、古銅色的皮膚和一臉憨厚的靦腆。再平凡不過的他,卻一直是我心中的一棵曠世巨樹;年幼時如此,年長時亦如是,生前是標竿,往生後依然是心底永遠的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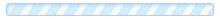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