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琳,欲去揀螺仔無?」
我迷濛睜眼。
太想睡了,下意識就想埋回被窩裡,拒絕她。
她不放棄,再一次搖晃著我;這回她甚至掀開我的被子,「有你上愛的牛罵仔喔!阿嬤佇土內底埋兩粒,誠大粒喔!」
她用手比出寶螺的大小和形狀來。
對了。是自己昨晚睡覺前跟她說的,早上她出門前一定要來叫我起床,我想知道她是去哪裡撿來那些寶螺的。
駝著一座星河般的半圓形寶螺,是她在海邊沬(bī,潛水)石花、敲海膽、拔紫菜的閒暇之餘一粒一粒收集起來的。剛撿回來的貝殼還是活體,為了保持外殼的亮麗,她會將寶螺埋進土裡,等待腐肉在泥土裡被細菌腐蝕殆盡。
小時候,看著她挖出泥土裡的寶螺,甚至一度以為寶螺是長在土裡的。
毋是喔!她解釋這些寶螺是怎麼來的,於是乎我便討著她,也要跟她去「牛罵仔的家」一探究竟。沒想到要如此早起。剛觸碰到寒意的身體立刻窩回被子裡,動作十分不情願。
終於起身後,天已經迷濛亮起。
清晨的海面才剛照上新一輪的陽光,腳印在琥珀的月色中踏出深淺不一的步伐。她走在前頭,牽著我跳過淌在礁石上的浪。
不是每一次撿貝殼都很順利。她說大的牛罵仔要更靠近海的地方才有,甚至要潛水下去石礁底部才摸得到,而我太小,根本跳不過礁。頓時有種被欺騙的感覺,我轉頭要走,她拉著我說,「以後阿嬤若是有揀到閣卡大粒的牛罵仔才攏互妳。」然後帶我在岸邊撿拾一般像寄居蟹類的小貝殼。
「你愛揀誠濟互我喔!」
「好好好。」
她如此答應。可隔一日又騙我說要帶我去撿寶螺,再次將我從被窩裡叫了起來,結果還是如同前日,跺著腳跟在她身後,踩踏浸泡在海水裡的自己的影子。
始終不明白,她為何總愛趁著大家熟睡時,獨自帶我到浪花的前頭,只為追逐一次次太陽升起前的破曉時分。
阿嬤晚年中風,意識還算清楚時,她用著含糊不清的語音告訴我,家裡的哪裡哪裡有牛罵仔,是她特別藏起來的。土裡,陶甕裡,塑膠袋裡,餅乾鐵盒裡……是她悄然無聲的用了大半輩子,在海蝕坪臺上,在浪潮間隙中,拾滿了。
後來,她的記憶越來越模糊,也逐漸消失。
同時也忘了,我已經長大了。
《曙光》作者導讀
馬崗,有臺灣極東漁村的美名,迎接著臺灣本島每日清晨的第一道曙光,但在歷史的地圖上,它彷彿被遺忘在時空裡,與世隔絕,悄然無聲的消失在浪潮的喧囂聲中;唯一能看見它歲月刻痕的,是那一間間錯落不一卻屹立不搖的石頭厝。
石頭厝是先民適應環境,就地取材而成,住宅型態是由海岸砂岩打石,彼此換工互助而成的一自然聚落,見證著空間中聚落與人文歷史的形成。這是有形的文化。
無形的文化來自於「記憶」。
一篇篇記錄馬崗人物的故事,也是一封封來自於馬崗海洋的情書;是手札,也是回憶錄。與個人經驗為主線的回憶錄不同,這是以「空間」作為回憶錄的主角;最大的特色在於,它是在地居民複數記憶的對話與地景人文的重構。透過實地踏查、訪問,以真人真事為基礎而寫成的紀實小說。
文化保存除了有形的建築物,也應該包含一個「活」的聚落型態,它既能以動態的形式保存,也能以具有生命的面貌傳承。本書的四個章節:「乘風破浪」、「安身立命」、「回家」、「停泊」分別描繪了不同時代、不同緣分而匯聚在馬崗的模樣。
馬崗屬於第二類漁港,進行區域性的近海漁業,男女分工明確,出外討海人多為家中男性,或稱作漁郎、海男。海男的作業範圍,從港邊的九孔養殖,淺水類別的捕撈活動,到近海漁業等。「乘風破浪」中有與海搏命的漁郎,有抓龍蝦的潛水夫,幾乎每個漁郎都經歷過的海腳實習生階段,也有讓漁郎們休憩的柑仔店情報站。
馬崗的海蝕坪臺是物種豐富的潮間帶,因應四季變化,潮間帶上有不同的產物與植被。「安身立命」中有海女的採集型態,海物仔的特殊烹飪方式等,以及畢生都待在岸上的女人們的叨絮日常。
離開家後,童年的記憶會就此烙印。「回家」中有馬崗出嫁的女兒與外出的遊子們,他們所行之地不同,但不約而同,都思念著家。對童年的尋覓與淡忘,在重述中再次深刻。
馬崗近年來因觀光發展,遊客蒞臨,也為一成不變的居住型態增添活力。「停泊」中有到此一遊的旅人,也有從此定居的新住民。此外,秋冬時節,馬崗為東北季風的迎風面,藻類滋生,馬崗的空軍溝是浮游磯釣的兵家必爭之地,特有的黑毛引來釣友一搏。釣客、過客,都成了馬崗的新記憶。
《曙光: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最想告訴你的是:
我們在這裡,從未離去。
寫下一封封手札,
寄給你,
也寄給曙光。
——摘編自《曙光: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三民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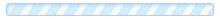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