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時醫生的診斷是,他得了青光眼,而且眼壓非常高,兩年之後可能會完全失明。隨著視力惡化,他再也無法用電腦工作了,而當時庫奇和妻子的房租等生活開支完全依賴他的收入。
遍尋醫生無果 轉向替代療法
庫奇開始想方設法尋醫問藥。他先是拜訪了當地十多位醫生,之後又去首都布加勒斯特找醫生,還曾出國求醫,但都無功而返。這讓他心中很焦慮,對未來憂心忡忡。對西醫治療方法不再抱希望的庫奇,開始尋求非常規的療法。
接受《大紀元》採訪時,庫奇回憶,當時他感覺最要命的並不是視力的喪失,而是巨大的心理壓力。為了紓壓,他開始轉向靜坐冥想。
庫奇先是練習瑜珈,也練過一些氣功,但那些方法所費不貲,而且讓庫奇一頭霧水——這是個大問題,作為計算機程序員,他喜歡對自己做的事刨根問底。
醫學外獲轉機 打開新天地
這時,一位朋友向他推薦了一種來自中國的功法——法輪大法(也稱法輪功)。上網查詢時,當看到法輪大法以真、善、忍原則指導修煉,功法中包括靜坐,那一刻庫奇意識到,這部法太好了。
法輪大法的五套功法,包括四套以站立姿態完成的動功,還有一套打坐功法,要求修煉者提升品行,其法理在《轉法輪》一書中有系統講解,於是庫奇開始閱讀這本書。
庫奇說:「看完這本書,我感覺看待世界的方式煥然一新,所有機遇都在我面前……我覺得這是真正的科學。」
為了體會《轉法輪》的內涵,庫奇一遍又一遍地閱讀著。一時間,庫奇能夠理解發生在自己童年時代的很多事情了。他小時候經常被人找碴欺負,但他從來沒有想報復,心中總是希望人與人之間能夠更好地相處。
走出陰影 發現人生意義
庫奇出生在共產主義的羅馬尼亞,從幼年時起,他心中就常疑惑,為什麼政府總在宣說我們需要建立和諧社會,到頭來人民的生活卻苦難連連。
他還記得小時候,晚上8點過後就會斷電;在雪中排隊買麵包,隊伍有1公里長。「但因為我出生在那個環境裡,所以不覺得有什麼不正常。」直到1990年他去匈牙利待了兩個月,這才發覺,冰淇淋不是冰和水的混合物,麵包也不是硬如石塊。
他更記得,「人與人之間有一種普遍的不信任」,這樣的心理陰影甚至延續到今天的羅馬尼亞。庫奇說,那時大家都傳:四人中就有一人是安全機構的特務,負責隨時匯報身邊人的「不當言論」。即便是面對朋友也無法交心,冬天家裡供暖中斷也不敢抱怨。
隨著年齡的增長,他對社會越加失望,看不到改變的希望。「那段時間我覺得人生沒有意義。一開始我希望社會能夠變好,令我難過的是根本就看不到出路。」他說。對社會環境的焦慮也影響到了家庭生活:雖然結婚多年,庫奇卻不想把孩子帶入在他看來充斥著暴力的腐敗世界,他擔心自己無法把孩子養育好。
而開始學煉法輪大法後,庫奇的想法完全變了。「讀了《轉法輪》,我想,現在我知道該怎麼做了。」他說,「當你改變觀念,換個方式看世界,可以說世界就已經變得不一樣了。」「我茅塞頓開。我發現,如果從不同的視角來看待事物,你會看到世上的一切都有其原因和意義。」「我再也不怕出門,不怕與人交談之類的事了。我變得樂觀起來,我找到了人生的意義。」
從過去凡事只考慮自己,到現在處處事事替他人著想,庫奇分享說:「如果我覺得自己要說的話可能傷害到他人,我會三思。以前我覺得自己是個很獨立的人,並不需要別人,現在我會盡可能避免傷害到別人。」
在家裡,庫奇再也沒有與妻子爭執過;在公司,他著眼於鼓勵身邊的員工一起把工作做好。他坦承,以前的他總想在項目經理面前顯示自己技能高強。而最大的變化還是:他成了一個幸福的父親。妻子生了一個女孩,而庫奇有信心應對養育孩子的各種挑戰。
至於庫奇的視力,學煉法輪功之後,他把藥停了,視力反而慢慢改善。修煉一陣子,他的視力完全恢復了正常。多年後的今天,他仍然可以勝任電腦前的工作,輕鬆養家。
2011年,在一次接受公司安排的例行眼科檢查時,庫奇告訴眼科醫生,8年前他得過青光眼。醫生非常驚訝,提出再仔細檢查一下,隨後告訴庫奇,他從來就沒有青光眼,一定是誤診,因為得過青光眼的人,眼睛上都會留有疤痕。對此庫奇只是付之一笑,沒有和醫生爭辯。
讓更多人明白真相
從法輪功中受益的庫奇,在接觸更多法輪功學員後,也意識到發生在中國的對正信的迫害,他開始考慮「如何能幫助、能制止這無理的事情」。
為了讓更多的人認清共產主義的邪惡,他和其他法輪功學員一起在所在城市組織了「《九評共產黨》研討會」,市長也來做了演講。
有很多人問庫奇,為什麼要關注遠在中國的事情。他用馬丁·路德·金的名言來回答他們:「任何一個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對一切地方的公正的威脅。」
他認為,面對普世價值遭踐踏,面對對人權的侵犯,每個人都能做些小小的努力,不僅為了自己,也為了後代子孫,而這小小的努力就會給世界帶來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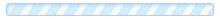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