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昭宇:「Tommi是開車去赫爾辛基機場接我的,當時正好是夏天,就是晚上不會有黑夜,24小時都是有太陽的白天。他準備從南部開車回北部,這樣我可以看到從南到北一路的風景。
「結果開到半路的時候我的生意合夥人就給我打電話,說你媽媽又被抓了。那個時候是2008年,當時很多人都被抓了,就是有律師、維權的人士、還有很多的法輪功學員,其中一個是我媽媽。」
看完整影片»
金昭宇妹妹金昭寰:「當時我是在放學的路上,回到家的時候,我就看到我家大院子裡面擺了很多我家裡的那些物品,我當時第一反應就是,是不是又來我家抓人了,因為我經歷過很多這樣的事情。我家是住在五樓,可是當電梯到四樓的時候,我就覺得我應該把自己藏起來,如果我也被他們帶走了的話,就沒有人告訴我姐姐發生什麼事情。
「我就從4樓的樓梯爬上去,在那個樓梯口,然後探頭看到,哦,家裡有好多好多的那些警察,非常地忙碌的在搬著我家的東西往外運,我甚至還看到他們,把我媽媽帶走的時候,還在我家門上貼了封條。
「我還聽到我媽媽到了最後還說,『啊,我小女兒她沒有家裡的鑰匙,她回到家開不開門怎麼辦?』但是我又沒有勇氣說衝上去,跟他們撕扯說放開我的媽媽,當時整個人就傻到那裡。」
金昭宇:「我當時的想法就是,我要馬上回去。但是Tommi說,『你現在回去,那不是直接進監獄麼?』那我當時就在想,既然我現在已經不在中國了,我現在是在一個自由的國家,我要為我媽媽做以前不可以做的事情。
「這張照片是我們認識的時候,2004年冬天的時候拍的。」
金昭宇丈夫Tommi Ylisirkka:「那是在鄭州的一間酒吧,我們初次見面的地方。我看到一個非常漂亮的女孩,她有點害羞,因為她說不了幾句英文。
金昭宇:「然後Tommi就走過來問我要電話號碼,呵呵。」
Tommi:「說不上來為什麼,就是想多瞭解她一些。」
金昭宇:「當時沒有給,但是後來給他了。
「他一個外國人人生地不熟,在當地也沒有朋友,他一趟一趟的來看我,堅持了四年,就給我感動了。
「那個時候是我生意做得最好的時候。大概19歲的時候,是我的一個朋友借給我了4000塊錢,讓我開始的。我是在一個服裝街上租了那個服裝店的一面牆,然後過了幾個月以後,生意的成本就回來了,然後就開了一個店。過了幾年又搬到更好一點的地方,後來就開了自己的專賣店,有自己的品牌,商場也有專櫃,給媽媽還買了兩套房子。
「我小時候對媽媽的印象,她非常的嚴厲。當時在廣東的時候,我父親有了外遇,我母親又一個人帶著我和妹妹去了另外一個城市。
「我媽媽那個時候身體越來越差,臉上就開始長很大很大的斑塊。後來去檢查,去了一家醫院又去一家醫院,去了有五家醫院,結論都是一個,就是她患上了肝癌。醫生都勸她說:『哎呀你不要治了,因為這個第一很花錢,第二根本都治不好,你就剩一年了。』
「當時(她)練的是另外一種氣功,但是練了很多年都沒有好,也是每天一大早就要去公園裡煉功,然後旁邊就是煉法輪功的。後來就有一個阿姨就介紹媽媽煉法輪功。她煉了幾個月就好了。
「她不光是身體好了,她的脾氣也變化很大。她以前是對我很苛刻的一個人,脾氣也非常的暴躁,但是煉功以後,她最大的變化就是她的脾氣變了,就變好了。」
沒過多久,中共開始了對法輪功的全面鎮壓。
金昭寰:「我一次又一次的看到我的媽媽被抓走,然後被迫害,迫害得奄奄一息之後,就被丟回來。姐姐很辛苦的工作,然後還要操我媽媽的心,還要跟那些警察就是打交道,還要跑關係,還要送錢、買禮物給他們。
「零五年、零六年的時候吧,好像是跟媽媽一下分開三年之久,第一次重逢,我們又一家人聚在一起過新年。就感覺,啊,好像媽媽這次放回來會永遠跟我們在一起。我們家裡買了好多好多好吃的,然後對我來講就感覺已經很幸福了。」
金昭宇:「因為我的媽媽和我妹妹在中國,我的生意也在中國,我的根就在中國,所以我在想,我永遠都不會來芬蘭。」
「Tommi為了要跟我在一起,後來他就嘗試在中國留下來,我們就去辦很多手續,但是他們都暗示就是要給他們請客啊、送禮啊,這就讓Tommi很反感。」
Tommi:「我們芬蘭人很直接,需要什麼就直說。但在中國,你必須來點私下的東西,得請客吃飯之類的。」
金昭宇:「那段時間我們就決定要分手。後來我覺得如果放棄這個人太可惜了,想要來看一看,看一看芬蘭到底是個什麼樣的國家。」
金昭寰:「送她走的那一天,我的記憶非常的清楚、深刻,因為那天我和她在一家飯店吃飯,那家飯店打烊了,燈光已經關掉了一半了。總感覺姐姐出國了,去見我未來的姐夫,會很開心的事情,可是總有一種不祥的預感。吃的飯,是火鍋,但是總感覺冷冷清清的。」
金昭宇:「抓媽媽的當天,家也被抄了,然後他們把媽媽綁架走以後還要抓妹妹,抓我妹妹的目的就是想抓我,說我是海外反華勢力。
「我媽媽就現在這個時候我媽還在跟他們講,她說:『我女兒那個時候是去看她男朋友的,怎麼會是反華勢力呢?』然後他們說,『她就是!』」
金昭寰:「2個月之後,我在姐姐店裡,國保大隊的人就突然闖進來抓人。工作室也去抄過一遍了,家裡也去抄過一遍了,什麼都沒有找到,他們就把我帶到了翠花路派出所。說今天一定要問出來她的姐姐去了哪裡。他們就讓我坐在那個審犯人的那個凳子上,但是我當時的那種感覺就是,覺得那個凳子,好像非常非常的髒,是給壞人坐的。
「我是很禮貌很尊重的,我說,『叔叔們』,我說,『阿姨們』,我說,『你們也有你們的家庭,你們想一下,如果你們得了癌症,又不知道該怎麼辦,可是突然有一天你們接觸了氣功,比如法輪功,你們身體變好了。可是這個迫害就是這樣誣陷,你們並沒有想說去跟政府對著幹,你們被抓走了,你們的孩子現在就像我這樣,落到這樣的處境,你們會怎麼辦?』他們當時就沉默了,然後就突然就很凶的說,『你今天如果不把你的姐姐的下落告訴我們,你就別想走出去!』
「從我上午十一、二點就被他們抓走,然後帶著一直在找,到下午五、六點被他們關到這個警察局,又關到八、九點,當時我記得好像天已經很黑了吧,有一個警察阿姨就走過來,她看上去像是領導人的樣子。她就說,『你到底還說不說?她說你不是很想你的母親麼?怎麼樣,我也把你送到監獄跟她關在一起好不好?』
「當時我就看到這個阿姨她的小孩,七、八歲的樣子,好像也在等著她回家,我當時心裡就想,要不你就把我給送到監獄去好了。我說,『我不希望你的孩子,跟你在這裡一直等,我不希望因為你們做這樣的事情,然後影響到你孩子的正常生活,因為她明天還要上學。』
「我當時這麼說的時候,她就一下子就愣住了,她就非常的激動,她說,『那你為什麼,你明明知道我在這裡等你,你為什麼不趕快告訴我呢?』我說,『我確實不知道,我要怎麼回答你?」她當時就說,『我現在把你放回去,你要是看到你的姐姐了,一定要趕快聯繫我們。』」
金昭宇:「手把鑿開了嗎?
「不戴手套可以伸進去。」
2009年,金昭宇和Tommi在一個芬蘭小鎮登記結婚。
金昭宇:「結婚當天我穿的是一件白顏色的毛衣,Tommi穿的是一件黑顏色的毛衣。我們是在市政廳結婚的時候,是神父找來的兩個證婚人,我都不認識。當時覺得很遺憾吧,因為結婚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件事情,我媽媽和我妹妹都不在身邊。
「赫爾辛基的法輪功學員為我們辦了一個小型的慶祝會,是在一個法輪功學員的家裡,她們為我們做了蛋糕,做了很多菜,還有餃子。
「當時也沒有這個心情跟我丈夫去度蜜月,心裡就想著趕緊能夠把我媽媽營救出來,所以就找了當地的媒體和大赦國際,開始這個營救的工作。」
Tommi:「我對儸瓦涅米這裡的一切很清楚,我們通常的營救方式就是給陳真萍本人寫信。這是其中一種形式,表示她並沒有被遺忘,在海外也有人知道她的案子,想知道進展情況。」
金昭宇:「當時因為警察要抓她嘛,所以妹妹也不敢回家住了,我跟合夥人就幫她在外面租了一個小公寓。」
金昭寰:「大概兩天以後吧,一天晚上,我就聽到有非常急促的那種敲門聲,然後我就隔著門偷偷的聽,我就聽到有兩個男人說話的聲音,他就問那些走道的鄰居說,『你們知不知道這裡頭住的是一個小女孩?』然後說,『你們知道她經常回家麼?還是怎麼樣?』那些鄰居也不熟嘛,就說,『不知道,我們不知道。』大概過了一個小時之後,他們也沒有破門而入,就說要不我們晚一點再來吧。
「即使這麼恐懼的感覺,我也沒有想到要離開中國,因為我想我的媽媽她還在這個城市,我還是跟她在一起的。」
金昭宇:「後來他們連那個小公寓也不放過,也找到了那裡,我們就想這樣妹妹太危險了,就給她辦了去馬來西亞的簽證。」
金昭寰:「在白雲機場登機的時候,警察一查我的護照就說,你要跟我來一個地方,就把我帶到了一個小房間裡。就說,『你在這裡等一下,我要去找一些人。』我就在想她是不是要去找警察,是不是不允許我離開這個地方,然後我就也是非常小心翼翼的,跟看小房間的那個人說,我說,『我能去一下廁所麼?』因為她並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她只是保證我不離開這裡,我就把我身上的行李都留下來了。我說,『你看,我東西都放在這裡,我還是會回來拿的。』所以她就放心我暫時離開。
「當我走到廁所的時候,其實離那個登機處有一段距離,那裡有幾個非常大的那種廣告牌,然後我就站到廣告牌的後面在看,我就發現那個把我攔下來的那個工作人員,她就帶來兩個高高大大的警察,然後一發現我不在了,他們就非常慌忙的想要找我,但是又知道看到我的物品在地上,就在想我是不是只是在附近,所以就開始拿著對講機在那裡說。我當時就想,不行了,我不能再回去拿我的東西了,我一定要離開。」
親人和朋友出於害怕都不敢收留金昭寰
她曾留宿車站 留宿24小時不打烊的商店
金昭宇:「我的妹妹流離失所大概一個月,是芬蘭法輪功學員,她幫助聯繫中國的邊境,幫助我妹妹偷渡到泰國。」
金昭寰:「那個時候大概是五月份的事,我們有很多人,好像除了我會講漢語之外,其他人他們都是講一些方言,我根本都聽不懂。
「不知道為什麼,到了一個地方之後,他們說這個地方必須要走路的方式,而且你要走的很快,但是我一向都是慢動作的人,然後我的腳一踩下去的時候,那個整個泥就包住了我的鞋子,我本來的那個步伐就已經很慢了,想要再把腳拔起來,就好像黏黏的,就更加慢了。
「但是我就看著跟我一起走的那些人,他們都已經漸行漸遠,他們的速度很快。我當時一心急,我就想我不管了,我就把我的鞋子脫了吧,但是誰知道脫了鞋子之後,很多的那些很扎的草還有一些刺就刺到我的腳上了……
「當時心情也很沉重吧,一想到媽媽還在監獄裡,不知道什麼時候能見到姐姐,不知道什麼時候這條路上會發生什麼事情,當時一看到人沒有了,我就緊張了,開始喊:『等等我!』
「可能他們也聽不懂我在喊什麼,但是他們應該能知道,哦,後面還有一個人,我就看到有一個阿姨飛快的跑過來,拉著我一起往前衝。當她手握著我的時候,我就有一種莫名的感動吧,覺得有一種鼓勵的感覺,就跟著她就一起就往前跑。」
2010年,歷盡千辛萬苦的金昭寰終於抵達泰國,向聯合國難民署申請庇護。
金昭寰:「有一天在跟姐姐通話的時候,她告訴我說,她在中國賣掉房子的房款被警察給沒收了,沒有任何理由的。我們的朋友也因為幫助我們被牽連,等於說是失蹤了,現在也聯繫不上她。我不知道是為什麼,覺得好像一下子什麼都沒有了,就心裡有種特別的難過的絕望吧,以前就是不知道天塌下來是什麼樣子,但那一次就感受就非常的強烈。
「最艱難的一段時期是,並不是說沒有東西吃,或者經濟上的問題吧,而是每天我也是在正常生活著,我在觀察周圍的人,我發現大家都在按部就班的過著自己的生活,可是我在想我的生活去了哪裡呢?」
Tommi:「(金昭宇)她幾乎所有的時間都用來聯繫芬蘭議員、國際大赦、還有媒體。」
大赦國際芬蘭分會成員Roope Kanninen:「我很佩服(金昭宇)她的平和和堅強。想想看她母親的遭遇,想像一下這對她來說有多艱難。她真令人欽佩。」
金昭宇:「芬蘭和英國的大赦國際還有芬蘭的外交部,都有聯繫泰國的UN。還有一些議員寫信,告訴他們儘快地批我妹妹來芬蘭。」
2年後 赫爾辛基國際機場
金昭宇:「等了那麼久等死了。」
金昭寰:「我覺得像在做夢一樣,當時在飛機上的時候就一直在掉眼淚,一直在哭,可是當我真的看到我姐姐的時候,我感覺內心是高興大過於這種悲傷,就是很開心很開心的,根本就哭不出來。
金昭宇:「等了她三年終於我們團聚了。然後身邊的法輪功學員他們也在哭。因為法輪功學員情況都是這樣子,家裡被迫害得家離四散。」
「(把這個)給那個翻譯啊,等會。你看這裡天還是亮的。」
金昭宇:「哎喲!痘痘臉了,我明天來擠啊。」
金昭寰:「你滿臉都是雀斑。」
金昭宇:「雀斑咋了?雀斑也比你的痘痘臉好。」
「哎喲!我的天啊……
「你看我剪頭髮了,你看我。」
「喏從這邊走過去就是市中心,唯一的一條步行街。」
金昭寰:「就這麼小的地方。」
「似乎從小到大,我們都在學習當中,都在聽到人和人之間應該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可是我真正的感受到這種感覺,是我踏上芬蘭的土地的這一步開始。人與人之間他們不會因為你的貧富而對你說話的態度不同。而且最大的感覺就是安全,我們居住的房子甚至不用鎖門。
「大概從我7歲開始,一直到19歲這幾年當中,一直都在經歷這場迫害,我根本沒有辦法集中精力去學習。」
金昭宇:「妹妹因為修煉法輪功的關係,她在小學的時候,老師就被警察要求在學校裡監視她,然後向警察匯報她每天的情況,她上學放學還被警察跟蹤。從小學一直到她上那個美術學院的時候,然後就被要求退學,就是因為修煉法輪功的關係。」
金昭寰:「當我來到芬蘭以後,我真的覺得晚上睡覺非常的踏實。在幾個半年之後,我覺得我是在慢慢的恢復吧,慢慢的體會到什麼樣才是正常人這種生活環境。」
金昭宇:「這個是我們去森林裡面採蘑菇,我們經常去採蘑菇的時候採完就現烤現吃。生一把火,把蘑菇在湖邊洗一洗,然後就拿過來,你看,這是洗乾淨的,拿個樹枝,拿個刀給它削一削就串著這個蘑菇,烤來吃。烤松茸。這是我妹妹。
「妹妹來了以後,過新年我們就開始包餃子了,恢復這個傳統。」
金昭寰:「當時去超市裡想買擀麵杖,回家自己包餃子吃,但是沒有找到。所以就在森林裡面發現了一根樹桿,然後就把它帶回家,用刀再把它削出來,這個樣子。
「我希望我以後的工作可以從事一些設計性的工作。
「這個畫的是芬蘭的國花,叫鈴鐺花。下面的這些,就是一些有關母愛主題的一些動物的這些畫面。其實裡面也有很多是因為我特別想念我的媽媽,所以我畫了一些。這個是,雖然自己是一隻很小的生命,但是它也要用它自己的方式來保護它的孩子。」
「姐姐,這條裙子是媽媽給你做的裙子嗎?」
金昭宇:「對啊!這個是媽媽給我做的裙子。」
金昭寰:「你們倆穿著一樣的衣服呢!」
金昭宇:「對啊,母女裝嘛!」
「我媽媽的藝術細胞特別的強,她會刺繡、鉤花、織毛衣。我媽媽會繡仙鶴和松樹,會繡龍和鳳還有鴛鴦。
金昭寰:「姐姐,這個大白兔的毛衣是誰給你買的?」
金昭宇:「是媽媽給我織的呀!
「還會自己設計旗袍,我從小穿的大大小小的衣服全部都是她做的。
「這張是單獨的一張媽媽穿旗袍的。」
金昭寰:「哇!好好看噢!」
大赦國際芬蘭分會成員Heli Honkasilta:「幾年前,我從雜誌上看到一條新聞,是關於這姐妹倆如何在儸瓦涅米團聚的。我當時被(她們的遭遇)嚇著了……我無法想像這麼可怕的事情發生在任何人身上。
「我能想像生命中揹負著這樣一段經歷有多麼艱難,但她講述的那麼有說服力,任何人都無法……那段經歷本身就把你吸引住了。」
金昭寰:「在記憶當中,我喜歡給我姐姐起一個綽號,叫女超人,但是我知道,在她的堅強背後,她有一顆非常非常脆弱的心,只不過她是不願意被這些困難去打倒的。她希望正面的去迎接和面對它。所以我看到她之後我也會覺得自己充滿了能量,應該更加的積極一些。」
金昭宇:「芬蘭北部的最大媒體和中部的最大媒體和芬蘭最大的電視台,都來採訪過,都報導過我媽媽被迫害的事情。
「芬蘭也有很多民眾自發的給我媽媽在的監獄寫信、寄卡片,要求他們釋放我媽媽。也不光是芬蘭的大赦國際在努力,還有加拿大的、西班牙的、德國的、臺灣的、美國的……很多很多地方,我都收到就是來自不同國家寄給我的這些卡片,我都發現他們都在默默地營救我媽媽。
「去年冬天的時候,我們收到(芬蘭)外交部的訊息,監獄給他們的反饋,會提前9個月給我媽媽釋放。」
金昭寰:「希望我的媽媽來能跟我住在一起,我能挽著媽媽的手,跟她一起去逛街。然後……因為這樣的記憶在我的印象當中從來都沒有過。」
2015年3月,陳真萍走出了河南新鄉女子監獄。
過去六年中沒有見過一絲陽光,她的眼睛會不時疼痛。
然而國安和610依然經常闖入她家,進行搜查。
2015年10月9日
經過艱苦的努力,陳真萍終於營救到芬蘭,姐妹倆終於和媽媽團聚。
——轉自新唐人電視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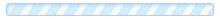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