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路幾番「停車暫借問」,才摸索到這個村園。繁花似錦迎面撲來,紅白相間,或含苞待放或落英繽紛。我們看得讚歎不已,唯一的遺憾是分辨不出什麼花是什麼花。
著急起來,只好憑著〈小放牛〉歌詞裡面的「桃花兒紅,杏花兒白,水仙花兒開」瞎猜一通。
下山之後,趕緊向學園藝的朋友虛心請教,「憑顏色認花」的自白卻被大大恥笑一番,順便聽了一大套有關花朵「單瓣」、「複瓣」的教誨。
因為這件事,使我想起一次和徐仁修交談的經驗。
一回和徐仁修約在台大校園,他拿著一落手稿,寫的正是「牠們哪裡去了?」二十年來在台灣日漸消失的好些動物的故事。
我隨手翻一翻,這些徐仁修筆下的童年玩伴,曾經是台灣隨處可見的野外生物,有些我竟從未見聞。這種知識上的隔閡,使我面對徐仁修隨口一句「請你指教」的尋常寒暄,而張口結舌起來。
徐仁修對都市土包子倒是見怪不怪,只是諒解地笑笑說:
「你在城市裡長大的,難怪不熟悉。」
也許是這段緣故,隨後我們在台大校園的漫步談話中,徐仁修一路向我指點各種草木花樹。在他是俯仰之間隨手拈來;在我則自覺尷尬而格外認真,竟像上課一般。
這個校園我在念書時候來來回回,當年無論椰林大道或杜鵑花叢都滿溢著年少輕狂的夢想,一切理想飛揚在雲端,從來不曾駐足留戀身邊的風景。當然也從來沒想過,我們腳下一概以「野草」通稱的很多植物也各有名目。
我寫文章,不可能以自暴短處為樂,談起這些讓自己也尷尬的經驗是有感而發。
現代人與自然生活疏離,原是所謂文明世界的通病,所以才有《鱷魚先生》電影的大行其道,算是對自己的嘲諷。但在台灣的例子裡,比起其他社會更加病症嚴重的原因之一,可能出於對自己生長環境的輕忽和不了解。
徐仁修寫的這些動物,曾經在人們生活周遭出沒,有些甚且為台灣特產,但漸漸由於社會工業化和都市化而消失。現在的孩子,不但無法在真實的生活環境中與牠們為伍,甚至少有機會透過學校教育間接接觸。
了解不夠,自然疼惜不夠,想像不出也感受不出台灣的特色。台灣環境千瘡百孔,自然和人文的生態一樣被破壞很厲害,實在是由於教育中沒有培養愛護生活社區的態度。
一回看一個報導,有人因為對台北縣、永和地方的感情,設計了一個「陽光小子」的方案,照顧永和的孩子。我當時很感動。我在永和出生、長大、居住二十多年,一回和童年的朋友談起小時候的永和,記憶所及不外燒餅油條、中興街的彈子房、竹林路的大水溝等等。
再往下想,對於永和的自然、人文、社會景觀的特色,竟然說不出究竟,很久以來,永和的市街招牌,看起來和新莊、板橋、桃園並無二致。那時候我忽然恐慌起來,害怕若有一天鄉愁不像余光中說的像一枚郵票,倒像沒貼郵票的信封,來來去去寄不回家中。
所以,桃花兒紅、杏花兒白,不經意唱唱也就算了。知識的缺口,不要讓它成了感情的缺口。
——摘編自《媽媽終於可以隨心所欲了》(聯經出版公司提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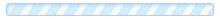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