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知等到女兒們出嫁的第幾年,有了孫子孫女,阿利才重新感覺到熱鬧。
那是三女兒出嫁後難得回家的日子,聽說這次也會帶回三個孫女,他作為孫女們口中的「海邊阿公」當然要展露一番身手。
冒險放風颱綾仔那次,已經過了快七年,雖然是同一艘舢舨,但阿利的體力已經不如以往。平常也只是偶而出海釣個花枝消遣。但是敲揖仔(chhip-á,藤壺)這種小事,還難不倒阿利;別忘了,他可是曾經被人稱做是「天公仔囝」的人呢。
「阿利伯,閣出海釣花枝喔?」
「我欲去敲揖仔。」
「這陣水焦矣,欲去愛緊去。」年輕人說著,阿利已經發動馬達。小小的舢舨駛出漁港。
敲揖仔的地方離港口不遠,就在雙礁仔。
雙礁仔顧名思義,就是有兩粒礁石,前後各一粒,中間水流過的溝就叫空軍溝;據說空軍總喜歡跳這條水流玩水。那是在民國七十年以前,關島作為防衛站戰線,美軍視東北角為軍事重地,後來關島撤軍,東北角的美軍撤走後,基地便留給了後來的空軍。當然,玩樂的場所也是。
雙礁仔再往外海去一些,就是雙尾礁仔,再來是紅礁仔,那裡也有不少事故,算是馬崗海岸線的最外圍了。
阿利的舢舨沒有出紅礁仔的範圍,他知道哪些地方得避開。
舢舨順利停在雙礁仔旁,他下船,拿出鐵撬,在礁石上敲敲打打起來。
女兒雖然從小在海邊長大,吃過不少揖仔,但他相信生在屏東的孫女們一定沒有吃過。阿利現在就能想像,孫女們看見這些像小火山的「石頭」,一定會驚喜得大叫。
如此想,阿利敲著揖仔的動作,就更加賣力了。
終於裝滿一袋揖仔後,阿利有些失落,他本來以為能敲到更多的。可眼見日頭漸大,開始照得他兩眼昏花,真的不得不停下了。
船在礁旁晃動,阿利拉住船的繩索,將船拉近身。
原以為一袋揖仔沒多少,卻沒想到重量比想像中重。拉住船後,阿利重新揹起揖仔。但也不知道是剛才低頭時,被烈陽照得昏頭,還是真的雙腳無力,身體站起時,微微搖晃著。
阿利想,要從船的肚子邊爬回去怕是不容易,如果腳沒踩好,掉進海裡可不是開玩笑的。他看見馬達的地方有個比較低的洞。如果是從船尾上去,應該比船腹邊還要省力吧?如此盤算時,腳已經跨了出去。
船突然晃了一下,阿利的腳只來得及上去半截。
他趕緊抓住船身上的平衡桿,屁股勉強抬離海面,可伸進去船身裡半截的腳,卻找不到施力點,無法出力。整個人就像是握住單槓那樣,撐在半空中。這時如果鬆開手,別說屁股了,連頭都會栽進水裡。他沒有多餘的力氣將身體盪回船裡。體力開始漸漸不支,好不容易挪上船的腳竟然還卡在馬達間。
不得不承認,自己早就沒有吊單槓的體力,也早就不年輕,無法如同過往在浪尖上逞勇。
阿利上下兩難,只能撐著。
海浪越打越高,已經來到下一回的漲潮。
這跟阿利原本預想的不一樣。他本來以為頂多一個小時就能完成工作回程,等著女兒女婿和三個孫女回來,然後讓妻去清洗這些揖仔,也不需要太多料理的工序,只要清蒸就很好吃。
從現敲到送上盤中,不超過半天,這是最新鮮的。
孫女們一定會對這鮮甜的海味嘖嘖稱奇,然後囔著「海邊阿公好厲害」。
海水浸到了阿利的半身。
耳邊孫女們的歡笑聲彷彿越來越靠近,從早上接到女兒說出發的電話到現在,已經過了六個小時,如果路程順利,應該已經下62快速道路,正在濱海公路上了。
浪越來越高。
阿利敲揖仔的雙礁仔已經被海水淹過一半了。
握著平衡桿的手忍不住發抖抽搐,氣喘的舊病也開始隱隱作祟。
要不要鬆開手,賭一把?如果頭栽入水裡,還能憋多少氣把腿從馬達的洞裡抽出?還是要放棄,乾脆剪掉腰上裝著揖仔的塑膠簍?
雙礁仔完全沉進水裡了。
阿利身上的汗不斷冒出,抓著平衡桿的手心黏膩滑溜。
他似乎錯過選擇了。
眼下,不管是要賭一把,還是剪掉簍子,都沒有機會了。
阿利閉著眼,孫女們的嬉鬧聲再度靠近,很清晰,就像是在眼前那樣,在房子前後追趕著,依舊喊著他「海邊阿公」。
就在孫女的聲音中,阿利突然聽見了喊他「阿利伯」的聲音。他無法轉頭確認是誰,艫仔的引擎聲便停在了阿利舢舨的旁邊。
是剛才出港前小聊過的年輕人,說是注意到了阿利出港時間過長,有些擔心才開船出來繞繞。沒想到被他看見這一幕。
年輕人單手有力,手撐著阿利的背。
阿利有了支撐,很順利就翻回船板,發抖的手腳不太聽使喚,爬了好幾回,才終於在船板上坐穩。坐回船裡的第一件事,他拉起與他同時浸泡在水裡好一段時間的揖仔,甩甩水,與自己一同,安穩的放在船板上。
確定自己真的是回到了船上後,阿利驚魂未定,愣坐了許久,不斷喘著氣。終於把氣順平了後,才緩緩道,「毋通佮阮厝內的人講,知無。」
年輕人點點頭,什麼話也不說。
阿利的船跟年輕人的船一起回港。
同時間,孫女們也到家了。
——摘編自《曙光:來自極東祕境的手札》(三民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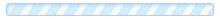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