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三嬸婆一家尚未遷居北部之前,廚房還完好無恙時,我曾去過很多回。大灶依稀記得是在西側小窗邊,設有大小兩門灶,灶上豎有兩支煙囪,斜斜穿越屋頂而出,那時家家如此。每當炊煮時刻,左鄰右舍炊煙裊裊,此起彼落,好不詩情畫意!灶臺上堆著鍋碗瓢盆和調味料,灶門前則是成堆的稻草柴火。「民以食為天」,所謂柴米油鹽醬醋茶,哪家能不如此?
出了廚房門外三五步之遙,有一口矮矮的、水量充沛的水井,外壁用水泥敷得相當平順,真的去打水時才發現內部完全是由大小均勻的中形卵石層層疊上來的。整齊圓滑的卵石因為水量充足而長年潤澤,似裹著一層薄薄的青苔。
平時取水時,一個空桶打下去,兩三下便可把滿桶水拉上來,尤其是大雨滂沱後更是隨手可得,我很喜歡去那兒洗東西,除了取水不費力,它周邊敷的水泥平臺微微的做出斜度,十分利於排水,這邊舀水一沖,那邊很快的就流逝得無影無踪,可見當初造井人的用心。
那時家家日間都不閉戶,大中小門都大大敞開。我如果要去洗什麼,只管穿門越戶,若恰巧遇到誰,打聲招呼就行,不過這是很熟的自家人才如此,不很熟悉的還是很守禮儀,不敢造次隨便進別人家的。
去三嬸婆家作客
三嬸婆和我祖母是妯娌,她丈夫排行老三,所以我們稱她三嬸婆。她一家人都很熱情,記得小學二年級左右,有一次,她們家要採收花生,一家人紛紛戴上斗笠、女性則頭罩花布巾,穿袖套,帶上扁擔,挑著高柄大小竹籃,說說笑笑的準備出發。
她們一家人那種「貧不憂、苦仍樂」的精神讓我欣羨不已,我心血來潮也想去幫忙,三嬸婆當然很歡迎,讓我回家說一聲,和他們一樣,拿著道具混入隊伍中,出發時還頗有點兒浩浩蕩蕩、大軍出征之感。
到了田邊,大人先下去一把一把的把整株花生拔起,漸漸堆出一堆堆帶果帶葉的花生,孩子們則一邊嘻哈談笑,一邊抓著整株植莖,就著籃子細心的三顆、兩顆的把比較成熟的花生摘下。碰到整株都飽滿熟透的,那就一把抓起拽下,好不快哉!
其實我自知醉翁之意不在酒,感受他們家的親和力是真,幫忙花生收成倒是「貨真價實」的假。
做到天快黑時才收工,回家後到井邊打水把泥手土腳一一洗淨,剛把東西放好,三嬸婆的兩個孫女阿文阿玉(一樣是小學生)就來叫吃飯,什麼!吃……什麼……飯!摘不到半籃也請吃飯?!我老媽在一旁(她平日一得空就編草帽,賺零錢補貼家用)笑笑的答腔,「妳幫三嬸婆拔花生,她請妳去吃晚飯啦,家家都這樣的,去吧。」我的疑惑才稍稍解開,原來成敗不在多與少,而是以有與無來論定。
到三嬸婆家之後,另一驚奇又接踵而至,方形沒上漆的粗厚木桌已擺了幾個陶碗裝的菜餚,安置在扁豆棚下,旁邊還有未就位的長板凳條。
可能扁豆種植已久,被採的差不多了,豆筴和紫色小花稀稀疏疏的,但仍微微透著不屈的氣息,緊緊的攀著竹架。這時,我看到牆邊靠著好幾大綑枝葉雜亂的花生植株,沾著土的淡黃花生果實夾在焦綠的枝葉中,顯得格外可愛。我聞到了花生株散發出一股生土氣息,阿玉立刻察覺並向我解說,為了快點完成這份收益,他們家大人不惜帶回整株花生,挑燈夜戰(我們幾個小孩回家時跑在前面,並未察覺大人在後頭做的這些)。
夜幕漸漸低垂,姐姐阿文適時扭亮了懸在柱上的燈泡。昏黃的燈泡有點暈濛濛的,藉此,吃飯時才看清眼前的菜色,一盤蘿蔔絲炒蛋,一碗豆腐、煎得有點焦黑的小紅魚、炒扁豆和空心菜湯。三嬸婆和阿嬸一疊聲的招呼我要自己夾菜,免客氣啦!
泛白的木桌上雖只有幾道簡單的家常菜,至今,我還記得那煎乾了的蘿蔔絲炒蛋,配上白米飯是多麼可口……
柴火也有令人懷念的故事
那堆綑綁堆置整齊的木柴很明顯是用電鋸從圓木四周裁切下來的剩餘材料,除了當柴燒之外,沒有其他用途。那時還沒有瓦斯,人們也不時興燒煤炭,大都用大灶燒木材,或從海邊檢漂流木燒火煮飯。而那一大堆木材其實是友情相送,很珍貴的。
當年我們七個孩子漸漸的長大,高中大學專科一路順利的升上去,上私立大學的也有,父親是個基層公務員,薪資微薄,每逢開學時,註冊費壓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於是賣田產,私人借貸、農會貸款等多管齊下。最後迫於經濟壓力,父親被朋友說動,貸款合資去臺中太平附近買了一大塊河川地,開荒種植,那真是「篳路藍縷,以啟山林」。
那時,老祖母約五、六十歲,身體還很硬朗強壯,自告奮勇去幫忙,十來個工人,煮三餐,洗衣服……打雜,備極辛勞,後來連大哥寒暑假也去幫工,大家這樣胼手胝足拼了幾年,發現獲利大大不如預期,再拼下去,也無法改變現狀。而且貸款利息又增另一道壓力,我老父於是決定把自己的股份「盤」給對方。對方我們叫他陳叔,是賣豬肉起家的,後來又開木材行,生意不錯,經濟上比我們家更有活水源頭。
陳叔很講義氣,也很敬重我父親,沒事時,常到我家陪我老父聊天。他是個直性子的人,嗓門特別大,偶而看到我們小輩的有不合常理的舉動或講了不得體的話,立刻毫不客氣的高聲指出糾正,所以我們都蠻怕他的,但內心裡卻是敬服他的。他也常送他家自產的東西,以卡車送來。小貓咪抓耙柴火的影像便是其中一個見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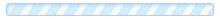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