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忽然感到好餓。打開頭頂的儲物櫃,找出來一個日清杯麵,再看看桌子上,幾顆農夫集市上買來的番茄,還有酪梨。可我想要吃一個麻婆豆腐。
「別人做給你的飯菜,永遠好吃的。」外婆說。我出國後除了去餐廳吃飯,絕少機會能吃到「別人」為我做的。無論是去朋友家,還是朋友來我家,都是我做主廚。偶爾吃到一次「別人」做的,會感動不已。也應驗了外婆說的話是真的。給自己做飯菜,努力想像把自己當作那個「別人」。左手接過右手遞來的,仍然還是自己。
外婆是我第一個飲食老師,也是那位給我做飯菜的「別人」。人生中第一道烤泥鰍,就是外婆做給我。那時候我應該是兩歲左右,被送到鄉下和外婆一起生活。有天她一大早就揹著我到橋背河邊,把我放在一塊大石頭上,自己挽起褲腳走到河裡。摸啊摸,捉到了一小籮筐。
為什麼我會有記憶呢,大約是因為那天河邊的風很涼,外婆的烤泥鰍很香。外婆把泥鰍烤熟後,仔細拔掉裡面的細骨再餵我。我還是被魚骨卡住喉嚨,張大嘴巴啊啊叫,爐灶裡火苗映紅外婆焦急的臉。
時鐘敲響十二下。不管那麼多,捲起袖子,打開抽油煙機、洗手、起鍋。開一罐豆瓣醬,再細細研磨花椒粒、拍蒜、剁蒜蓉。外婆從來沒吃過四川菜麻婆豆腐。她這一生只知道家鄉的味道。她最拿手的菜是糯米酒燉雞。
大學時代回鄉下看望獨居的外婆,清晨半睡半醒聽到她在天井抓雞,外婆一邊口中念念有詞:我孫女回來啦!大學生啦……一邊悄悄的走到雞群中,那雞被外婆一把抓住雙腳,咯咯直叫使勁撲騰掉了一地雞毛。到了晚飯,外婆驕傲的釀酒燉雞就端上了飯桌。到如今,是的,我才明白,世界這麼大,原來家鄉味道是最好。天下之大無奇不有,人真的並不需要什麼都知道。
想起二十年前外婆在家中去世,那晚她頭痛,閃電般抽著她的神經,我按摩她的肩膀來轉移一些痛苦,外婆手指著自己對我說:「怕是殺了太多雞,所以現在報應來了麼。」
「阿婆,被你殺的雞我也有吃,你我都信佛,放心,它們將來轉生或許會與我有緣。阿婆你應該已經轉生了吧,或許有一天我會在人群中認出你。」
「阿婆,我已經會做上百道菜了。我去過了地球上十幾個國家和城市,法國人吃鴨肉,義大利人吃麵條。」
「哈哈,你十分會,我早說過,你將來會在萬人之上。」外婆坐我對面,一身絲綢唐裝,雙手托著下巴,看著我碗裡紅彤彤的一片,笑吟吟。
要是在年輕時,我會嚇個半死。我會跳起來掐自己的胳膊肉趕走外婆沒死的幻覺。現在,我默默低頭,大口大口吃光碗裡每一粒飯。我願意,她就一直這樣看著我吃,我願意她與我就這樣坐到天明。失去了她,從此我不再害怕。
印象中從未做過一頓飯給外婆。直到她年邁,直到她去世。我住在父母家時,是媽媽做飯菜。我不靠譜,因此她也甚少讓我搭手。媽媽做菜在親戚中是有名的,她能半個小時內燒出四菜一湯。
我小時候住在那種共用廚房的集體宿舍,就有鄰居偷吃我家放在廚房裡的剩菜。被我發現報告給媽媽。她一點都不信我說的,因為那個偷吃的人是個大家公認的好孩子、乖孩子。等到他再次偷吃又被我看到,還當著我面得意洋洋了一番。我一個六歲小孩,自然是大人心目中的編故事好手,哪裡有什麼辦法。每次看他偷吃,我就雙手放在後背左手扭著右手,心裡禱告媽媽立刻趕到,能像孫悟空從天而降那就最好。
我大學同學也知道我媽做菜一流,全系同學輪番來我家吃媽媽做的菜,讚不絕口。包括我爸爸的同事、朋友,來我家吃飯的人更是數不勝數,媽媽總是說我們家是飯店和客棧。她總是臨下班前在單位就接到爸爸打來電話,說晚上多少人要來吃飯,要吃什麼。都是臨時決定,臨時編派,她照樣能準時開飯,滿足每位客人的胃口。
已經是最強高手了,媽媽做的飯菜有一陣子卻是尤其的不同凡響。那是我即將遠行前的一個月。酷熱的初夏,那一段時間我持續奔波勞碌,常常夜歸晚起,客廳餐桌上總有一碗葛根豬骨湯、蓮藕海帶湯、蘿蔔排骨湯,或者一碟欖角蒸鯇魚(草魚)、豉油雞、清炒甕菜。統一用蓋菜罩子罩上,天天等我。
至今回想起來,大約是她的飯菜比她本人更先獲知:我,即將一去不復返了。飯菜裡混合了深情、恐懼、驚嚇、懇求與不捨的味道,如同廟裡燒的香,又如那深井凜冽的水,詭異般的分外香甜。
——轉載自《新紀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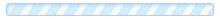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