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家楊照有篇文章寫到,他和朋友去史坦威鋼琴門市試琴的經過,故事大概是這樣的:他和朋友因好奇而走進史坦威鋼琴門市,接待的女士殷切的問他們想彈什麼樣的琴?他們說了想要入門款的琴。
於是接待女士說,她並不是問這個,而是問他們想彈出怎樣的音色?想演奏哪個作曲家的作品?後來,他們試彈了奧地利作曲家舒伯特與莫札特幾首曲子,並得到了啟示。
啟示簡單來說是這樣的,鋼琴雖是規格化的樂器,但因為製作材料、方法不同,儘管是同一廠牌、同一型號的鋼琴,所發出的聲響也各自不同。更進一步說,即便是同一臺鋼琴,不同時間、年分彈出來的音色也不相同。
史坦威鋼琴因為正視演奏者的需求,並協助他們找到最適合自己的鋼琴,因而成為鋼琴的首選廠牌。以鋼琴製造技術而言,史坦威並非無可取代,但因為這個附加價值,而使得他們的琴貴得理所當然。
楊照的這段經驗,頗似莊子寓言中許多故事,技進於道。然而,我們可能難以明白,為何藝術與道的追求如此純粹?捷克裔法國作家米蘭昆德拉《被背叛的遺囑》一書,曾提過一個吸引人的故事:俄國作曲家史特拉汶斯基因為樂團指揮安塞美想在他的樂曲加入一個停頓,他便不惜斬斷與對方長久的友誼。
追求完美看似藝術家的天職,但其實我們也理解,這些技進於道的無悔、固執與追求,在聽眾接受層面而言,也是極低的。
作家王文興覺得常用漢字不敷使用,進而造字;作家李永平翻閱《康熙字典》,尋覓生僻的冷字,鑲嵌進小說。這些擇善固執的作家認為,非得使用這些文字,方能精確表達小說的意旨。但在讀者眼中,那些被苦心找(造)出來的漢字,多半成為念不出來而被跳讀的字句,無法產生作家期盼的美學風格。
史特拉汶斯基樂曲被加入的停頓是否真如此事關重大?那也許只是幾秒的時間,在聽眾分心或瞌睡時轉瞬即逝。一如奧地利作曲家馬勒在吵雜的公寓裡修改自己的交響曲,置換某些樂句的配器,因而傳為佳談。但那些置換,對聽眾而言,是否真的影響深遠?真的被聽出意義?
這是個不易回答的問題。
史坦威鋼琴如此計較每一臺鋼琴獨特的音色,為演奏者量身挑選,但那音色、頻率的差別,對美學的執著,傳遞到聽者耳裡的效率,又是如何?
面對這個問題我無限悲觀,但米蘭昆得拉卻有個獨特的詮釋方式,他贊同作者的主體至上。因此,他嚴謹對待文字、嚴謹對待翻譯的語意滑動問題、嚴謹對待作者主體性的伸張。他的確是追尋著所謂的純粹和完美,因此,在史特拉汶斯基的事例裡,他完全理解,史特拉汶斯基非得跟朋友絕交不可。
但這個故事還有後話,晚年的史特拉汶斯基修改了自己的交響曲,他已絕交的指揮家朋友安塞美質疑他,認為他「無權」更動自己的作品,也不欣賞他的改作。
米蘭昆得拉則欣賞史特拉汶斯基的回應,他認為一位優秀作家的作品,既不屬於他朋友、不屬於他的國家,也不屬於全人類,作品只屬於他自己。作者隨時可以把自己的作品修改得面目全非,就像美國搖滾詩人兼歌手巴布狄倫每次演唱自己的作品都面目全非,就像武俠小說家金庸自己小說改編版本的毀譽參半。對此,我們也只能沉默。
如果說,藝術家、文學家有自己一套獨特的審美標準,儘管他的作品晚節不保,或是晚年漸於詩律細、文章老更成、後出轉精,都是一種對自己作品的自我責任,無須向誰負責、無須向誰解釋。
所以,我們雖可不欣賞金庸改寫自己早年的作品,我們雖可讚嘆馬勒對自己作品的堅持,但那些追求,皆是一種純粹性的追求與展示。一如每一臺史坦威鋼琴的音色,都等著合適的人來喚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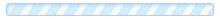 loading...
loading...



